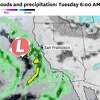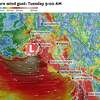劳里·史蒂夫斯(右)在旧金山第七街的帐篷外拥抱着她35岁的女儿杰西卡·迪迪娅,她无家可归,正在与毒瘾作斗争。
Gabrielle Lurie / The Chronicle毒贩聚集在第七街和Mission街,公开贩卖毒品。在他们脚下,人们吸着锡纸上的芬太尼,其他人则在打盹。人行道上点缀着帐篷。阴沟里堆满了成堆的食物残渣、垃圾和粪便。行人,包括一名推着婴儿车的妇女,为了超车,几乎突然转向进入第七街的车流中。
57岁的劳里·史蒂夫斯(Laurie Steves)站在商业和混乱中等待。
她35岁的女儿杰西卡·迪迪亚(Jessica Didia)对阿片类药物的上瘾已经毁掉了她的生活,她住在角落里一个巨大的灰色科尔曼帐篷里,帐篷放在关闭的古德酒店(Good Hotel)的遮天篷下。该酒店的网站仍然吹嘘它的位置“将城市最好的东西带到你的家门口”,但如果曾经是这样的话,现在肯定不是这样了。
- “芬太尼是历史上的敌人”:旧金山致命药物过量的新数据显示了流行病的走向.
劳里是西雅图郊外一家养老院的厨师,在得知杰西卡因反复发作的疾病住院后,他于1月2日飞往旧金山猛烈的暴风雨向城市猛攻。她想让女儿进去。
但她知道她的任务希望渺茫。她需要一步一步来。首先,她愿意带女儿去散个步。

劳里·史蒂夫斯看着她的女儿杰西卡·迪迪亚在市场南部的维多利亚马纳洛·德瑞夫斯公园里翻找毒品用具。
Gabrielle Lurie / The Chronicle“来吧,杰西!”她隔着拉上拉链的帐篷不停地喊着。杰西卡会回喊她正在准备。但之后她会大喊她找不到鞋子和烟斗。我们一直在等待。
劳里和杰西卡一年前出现在这个专栏里城市里芬太尼泛滥的时候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位母亲绝望地试图将女儿从无家可归和吸毒中拯救出来,但失败了,这种毒瘾现在正在全国肆虐,旧金山人对此产生了共鸣。读者们分享了他们的沮丧,因为这座城市似乎没有能力帮助像杰西卡这样的人,即使他们的生活在众目睽睽之下分崩离析。
劳里于2021年春天搬到了旧金山,在25岁的儿子扎卡里因吸毒过量去世后,她决心拯救女儿。但3个月的努力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劳里在物价高得离谱的旧金山生活不下去,杰西卡也明确表示她不需要帮助。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在一起争吵,劳里沮丧地离开了。2021年11月的短暂访问并未取得更多成果。
14个月后,我们又联系上了,我发现自己对某些事情会有所改变抱有新的希望。但无论对劳里、杰西卡还是旧金山来说,一切都没有改善。
杰西卡的日常生活——不仅在本专栏中曝光,还被试图帮助她的企业主亚当·梅斯尼克频繁发布到推特上的视频曝光——体现了这座城市的许多问题和紧张局势:吸毒过量危机,芬太尼的吸引力,的帐篷营地的法律斗争,疫情肆虐的市中心和城市领导层似乎无法在任何问题上取得进展。
尽管劳里和杰西卡的生活仍然停滞不前,但在过去的14个月里,旧金山一直动荡不安。就在第一篇专栏文章发表后,伦敦市长布里德宣布,“摧毁我们城市的胡说八道”即将结束田德隆有紧急情况但她未能迅速而有意义地改善该社区的警察配备,紧急命令也随之终止。街道依然混乱,尤其是在晚上,以至于附近的商人都要求这样做旧金山要偿还2022年的税收。
布里德在联合国广场开设了Tenderloin中心,为像杰西卡这样的人提供了一个获得帮助的地方。她并没有宣传它包括一个临时防止过量使用的场所,人们可以在监督下在院子里吸食芬太尼。12月初,布里德关闭了中心,她还没把它换成她保证会有一个真正的临床监督消费网站。
市长已经开放了更多永久性的支持性住房和治疗名额,但这个系统仍然很复杂,很难进入。愤怒的选民在6月召回了地区检察官切萨·布丁,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他对解决芬太尼市场问题不感兴趣,而新任地区检察官布鲁克·詹金斯在监禁毒贩方面只取得了很小的成功。
过去一年里,劳里和杰西卡最大的变化是一个令人心碎的变化:4月12日,杰西卡的男友阿卜杜勒·杜拉·科尔死于吸毒过量。2022年的城市毒品死亡人数还没有出来,但可能会接近600人,这使得三年来的总数接近2000人——比新冠肺炎、他杀和交通事故的总和还要多。
杜拉在旧金山长大,毕业于麦卡特高中,被佛罗里达马林鱼队选中打外场。但这个早期的希望变成了悲剧,他独自死在艾迪街(Eddy Street)一家单人旅馆的房间里,几天后他的案件经理发现了他的尸体。那年他46岁。
今年春天,我在熟食店(Deli Board)和杰西卡谈起了杜拉的去世。她经常去熟食店和朋友梅斯尼克(Mesnick)聊天。他给她苏打水、咸菜、薯片和现金。她让他录下她谈论自己生活的视频,并发布在他有争议的账户上,@bettersoma.批评人士称这些视频麻木不仁,具有剥削性;梅斯尼克说,他迫使人们近距离观看城市街头的苦难,这样他们就会向城市施压,要求干预。
杰西卡是一个有魅力、勇敢、机智的女人,她小时候参加过选美比赛,在学校里是啦啦队长。那天在熟食店,她戴着粉红色的猫眼眼镜,穿着紫色的紧身裤,但脸上的血色已经消失了。她说,没有了男朋友,她漫无目的。她的男朋友给她提供了一个断断续续的睡觉的地方,取决于前台接待员是否允许,还在街上给她提供人身保护和情感支持。
“太可怕了,”她告诉我。“我一下子失去了一切。我一直在等他骑着滑板车过来。我转过身,以为是他,但不是。”
在悲伤中,她没有依靠母亲的支持,只是在2022年亚当说服她用他的手机打电话给劳里时,她和劳里谈了几次。与此同时,劳里不断地想起她的女儿。
“每天,”她说。“只是洗澡或刷牙,我就会想,‘她多久没这样做了?’当我做食物的时候,我知道她会喜欢,我就会想,‘我希望我能给她带一盘这个。’”
去年12月,在她最后一次见到女儿一年多之后,劳里接到了亚当的电话。杰西卡在癫痫发作后住进了当地一家医院。劳里计划立即飞下来,但出现了感冒症状,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
当她的检测结果呈阴性时,杰西卡已经出院了,带着一张出租车代金券去了一个她没有使用的庇护所,她没有去过美沙酮诊所,她没有服用过抗癫痫药物。相反,她直接回到了她和一个朋友住在第七街和Mission街交汇处的帐篷里。
1月2日,劳里抵达了这座城市,在亚当的引导下,她很快找到了杰西卡的帐篷。它所处的地方曾经是一个宜人的角落,到处都是小企业,其中许多已经倒闭。在大流行期间,好酒店成为了就地避难酒店,这个项目肯定有助于拯救生命,但它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阻止毒贩占领人行道在外面。现在是空的。

杰西卡·迪迪亚(Jessica Didia)抽着芬太尼和可卡因的混合物,她的母亲在第七街的一家咖啡店里喝酒。
Gabrielle Lurie / The Chronicle劳里和杰西卡在帐篷里聊了一会儿,劳里答应第二天早上再来看她。第二天,在等杰西卡从帐篷里出来很久之后,劳里告诉她半小时后再来试试。我们回去的时候,她已经不在了。
劳瑞在SoMa四处寻找杰西卡,甚至在塔吉特百货公司的过道里找杰西卡,杰西卡坦率地承认她在商店里偷东西来卖芬太尼的钱。劳里说,她有时希望杰西卡会因为盗窃价值超过950美元的商品而被捕,这足以被视为重罪,并被迫在监狱戒毒。
在路上,我们看到灯杆上贴着宣传这座城市的横幅,上面写着“旧金山:领先于潮流”。
“是啊,没错,”劳里嘲笑道。“我没有看到同情心在行动。我没有看到他们为无家可归者服务投入的数百万美元。我对我在旧金山看到的感到厌恶,真的。”
我们前往熟食店,坐在门口,直到杰西卡骑着她的朋友帕里斯·维恩斯(Paris Vines)驾驶的摩托车出现。她走路不稳,说她感觉糟透了。她脖子上系着一个透明的塑料急救箱,里面有锡纸和香烟。
我们都去了街对面的公园。帕里斯试图说服杰西卡和他一起去一个收容中心,在那里她可以得到服务和庇护。在田德隆区流浪了十年之后,他说他最近在英巴卡德罗导航中心(Embarcadero Navigation Center)找到了一个职位,他很喜欢那里。他说,看着人们慢跑、上班、幸福地生活,感觉很好。
“与这座城市的其他地方相比,田德隆区就像一个恐怖故事,”他说。“这是地下世界。”
杰西卡似乎不感兴趣。劳里建议他们回她住的旅馆去看电影。或者喝杯咖啡。杰西卡似乎也不感兴趣。
“我们需要让你参加一个项目,”劳里告诉她。“事情会好起来的,杰西。”
“不!”杰西卡反驳道。
“你知道你会死在这里吗?”妈妈问她。
“所以?”杰西卡回答道。“不管怎样,我总有一天会死。谁不是呢?我已经死了100多次了,但我还在这里。”
她指的是用药过量然后又服用了纳洛酮。
“你晚上会很暖和。你可能是干的,”劳里说。“你可以有个家,有份工作,有自己的生活。”
“因为你说了这些话,事情就会发生?”杰西卡问她。“你不能让我希望它发生。”
杰西卡走开了,告诉她妈妈别烦她。
劳里回酒店睡了个午觉,但在凌晨3点半,暴风雨越来越近,她一下子就醒了。她在黑暗中走向杰西卡的帐篷,并提出为她和她的帐篷同伴安排一个酒店房间来避雨。但后来她找不到自己能负担得起的空房子。

杰西卡·迪迪亚走在维多利亚·马纳洛·德雷克斯公园外,一名男子昏倒在地。
Gabrielle Lurie / The Chronicle第二天,劳里回到帐篷,建议杰西卡去她住的酒店或去避难所,但杰西卡不想离开她的帐篷同伴去任何地方。劳里说杰西卡对她大喊大叫,骂她撒谎,说她会给他们买自己的房间。
“我不会坐在那里听它,”劳里说。“我只是走开了。”
劳里在第二天飞回家之前没有再见到她,他又一次失败了。
当然,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
代表SoMa的主管马特·多西(Matt Dorsey)说,他在熟食局见过杰西卡,她的案例表明,该市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结束露天毒品场景,要求对那些严重残疾而无法照顾自己的人进行治疗,并通过给人们现金奖励来鼓励其他人戒毒。他也很乐观加文·纽森州长的护理法庭计划迫使更多的人接受治疗。
多尔西说:“没有适合所有人的单一答案。“但我们有很多理由抱有希望和乐观,我们需要在很多不同的策略上尽最大努力,并不断尝试新事物。”
无家可归者联盟(Coalition on homeless)的负责人詹妮弗·弗里登巴赫(Jennifer Friedenbach)曾起诉市政府清理帐篷的行为,并成功获得了针对他们的禁令。她说,杰西卡的案例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提供适当的安置,大多数人都会接受庇护。她还说,该市的系统围绕着紧急情况——比如杰西卡的住院治疗——而不是提供长期、持续的护理。
Friedenbach说:“理想情况下,她应该与服务提供商和密集的案例经理建立信任关系,与她密切合作,找到解决方案。”
对亚当来说,杰西卡无家可归并不是主要问题。是因为她对芬太尼上瘾。他想看看加大对毒贩的打击力度并为使用者提供更多的治疗。
“我不知道你怎么能在帐篷里问一个吸芬太尼的人是否需要服务,”他说。“真的,她正在被芬太尼活活吃掉。这座城市很擅长伤害别人。”
劳里说她不会放弃。她说,如果杰西卡再次住院,她会立即飞过去,在她出院前接她,给她一个预先安排好的排毒中心的位置。不管怎样,这就是计划。
“我爱她,”她说。“我喜欢她的聪明和创造力。和有才华的。我想把这些东西都拿出来。我想看到她成为她自己。”
所以她继续等待。
希瑟·奈特是《旧金山纪事报》专栏作家。邮箱:hknight@sfchronicle.com推特:@hknights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