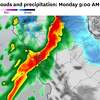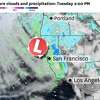2005年,在她无家可归之前,Kori和她的侄子在一起。
香农·米勒政策制定者和精神健康倡导者之间就是否应该对那些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进行强制治疗进行了辩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也是一个我纠结了多年的问题。
在我妹妹科瑞生病之前,她是一个正常、健康的年轻女性,有着光明的未来。她聪明、美丽、坚强、独立。她并不完美。她有过忧郁的时期。但她总是会振作起来,继续前进。她是个斗士。
然而,15年前,科里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开始用奇怪的口音说话,变得容易偏执和愤怒,她开始酗酒。我们认为酒精是问题所在,所以我们进行了干预。科瑞没来。
她失踪了六个星期,最后却被送进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的一家精神病院。她拒绝接受任何治疗,但情况稳定。医生的诊断是“精神崩溃,没有特别说明”。她一再拒绝治疗。在接下来的六年里,她不仅失去了理智,还失去了丈夫、家庭、积蓄、朋友和未来。
因为她是成年人,我们无力帮助她。我们只能在一旁看着她毁掉自己的生活。
直到科瑞威胁我父亲,我们才最终得到了她的治疗和更具体的诊断——患有精神病特征的双相情感障碍I型。这听起来很糟糕,但在我们的家乡亚利桑那州强制要求的药物治疗下,她又恢复了正常。她开始在社区大学上课,谈论她的未来。情况正在好转。40岁时,她还有机会重获新生。
她的康复很短暂。
亚利桑那州要求她接受一年的治疗,那一年一结束,Kori就停止了服药。她的智力下降得很快。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她大部分时间都过着街头生活——夏天在西雅图,冬天在凤凰城,其间还会去加州看望我。她乘公共汽车或搭便车旅行,靠我父母给她的少量钱生活。
时至今日,科瑞的行为依然不稳定。她与看不见的敌人战斗,逃离不存在的威胁,但却让自己容易受到真正的威胁——孤独、饥饿、抢劫、袭击和恶劣的天气。她经常发表恐同、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言论,这与她的本性不符。
街上的生活既不容易也不友善。这对她的身体造成了伤害。她的年龄呈指数级增长。
我父母试过很多次想收留科瑞。如果没有药物治疗,这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很困难的。除了严重的行为问题外,她还用香烟、酒精和可能的药物来自我治疗。她可能很有破坏性。
在过去的六个月里,科瑞一直住在门洛帕克,离我很近。她通常每天都坐火车在半岛上下穿梭,参观那些她在快乐时光中熟悉的地方。她经常去我们当地的咖啡店,那里的人都知道她的名字。她不肯告诉我她睡在哪里。有时她会简单地对我说一句“晚安,笨蛋”,跟我道晚安。有时她指责我犯了罪,说我应该被判死刑。
两者都让我同样难过。
我和我的家人试图找出她是否有资格获得残疾或临时住房,但我们没有真正的进展。她不会与心理健康专家或外展项目合作。他们一提起她就跑。
几周前,在一段异常平静的日子之后,我正在寻找她,我发现她被逮捕并关进了监狱。那天下午有个听证会,所以我去了法庭陪她。对她的指控很严重。她穿着橙色囚服,戴着手铐,从玻璃隔墙后面热情地向我挥手,她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陷入了麻烦,也没有意识到自己造成了伤害。
她被指控侵犯他人的公民权利,多次在他们家外威胁他们。我感到悲伤和羞愧,但不是难以置信。她的保释金为2.5万美元——对于她这种情况的人来说,这是一笔不可逾越的金额。
虽然科瑞应该进医院,而不是监狱,但也许这是我们目前能做的最好的了。
在加州,最近通过的《医疗法案》试图解决许多存在了几十年的心理健康缺陷和漏洞。它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多有待观察的地方,但它试图采取一种长期、全面的治疗方法,将住房、药物滥用和其他社会服务与临床护理结合起来。像我妹妹这样的人有法律顾问。有固定的检查点,有最终目标。并不一定要有迫在眉睫的威胁才需要强制护理。授权可以延长。
这部法律最打动我的是它所用语言的语气——同情。
《护理法案》只适用于那些像我妹妹一样患有严重精神障碍的人。在我的国家,它可能还要再过两年才能完全发挥作用。
我们将等待。这是我们对科瑞最好的希望。
香农·米勒(Shannon Miller)是精神健康改革的支持者,也是精神疾病患者的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