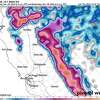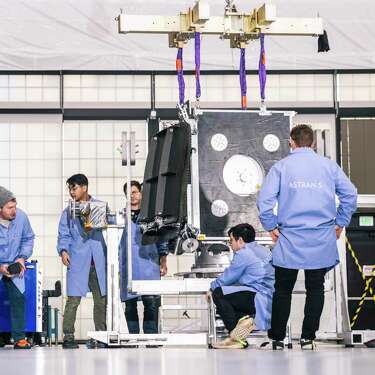Paxlovid可以帮助缓解COVID的症状,但对谁能得到处方有限制。
Brontë Wittpenn/The Chronicle我马上就知道情况会很糟。
那是一个炎热潮湿的夜晚——几乎有90华氏度——但我的身体却冻得不行。穿上运动衫,盖上毯子也不能让我暖和起来。另一方面,我的头却像着了火一样。我的体温超过了100华氏度,需要在额头上堆上冰袋来降温。咳嗽个不停。
我不需要测试来告诉我我终于感染了COVID。
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基本上像个隐士一样生活,以避免这种情况。当然,在接受了疫苗接种和增强后,我不认为COVID会杀死我。但我并没有金牌免疫系统;即使是普通的感冒也让我很难受。我以为COVID会让我病倒,症状可能会持续几周或几个月。所以我远离办公室、室内聚会和餐馆。健身房吗?不,谢谢。为了避免生病,多吃15磅是值得的。
但今年夏天是我姐姐的40岁生日th的生日。她和我的家人住在东海岸,正在举办一个盛大的派对。所以我决定离开我的洞穴,飞过去看看他们。
果然,另一个人悄悄出现在庆祝活动中,吮吸着咳嗽药水,向任何人保证,她不寻常的鼻音语调只是感冒。
它不是。我傻到就坐在她旁边。
第一个症状一出现,我就知道我有麻烦了。所以我决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弄一张Paxlovid的处方,这是一种抗病毒药物鸡尾酒,可以防止冠状病毒在感染的早期阶段在你的体内复制。严格来说,我不符合资格,因为我不到65岁,没有任何严重的合并症。但打寒战、剧烈咳嗽和发高烧肯定是有原因的,对吧?
显然不是。
当地药剂师不会和我有任何关系。紧急护理也不行。我打电话给我在旧金山的医疗保健提供者开了一张处方,但它也告诉我,我不适合服用Paxlovid,必须休息并度过难关。
所以在接下来的12天里,我咳嗽、出汗、流鼻涕,每天睡16个小时。我没有时间和家人在一起,我不得不不惜一切代价避开他们,不让他们生病——除了乞求食物和生活用品;他们居住的农村社区没有快递服务。
在浪费了一个假期,换了航班,又多请了几天病假之后,我终于在几周前回到了家。
同一天,我的伴侣开始出现COVID症状。
她也没有资格服用Paxlovid,在接下来的10天里,她一直在孤独的痛苦中煎熬。她的检测结果最终呈阴性,但我们都没能恢复正常。前几天在金门公园(Golden Gate Park)的一次温和的丘陵散步让我喘不过气来,就像刚跑完马拉松一样。那天晚上我八点半就上床睡觉了。
我不确定是哪一种变异导致了我们的死亡,但根据感染数据,几乎可以肯定是BA.5。现在,随着BA.4.6的发展——以及未来的变种——如果我们想像大流行之前那样自由地生活,我们还必须再次经历这一切吗?因为我没有生病的日子,也没有那个胃口。我不可能是唯一一个。
我希望新的欧米克隆助推器能打破这个循环。但如果不是呢?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存在像Paxlovid这样的抗病毒药物,可以在病毒传播之前阻止病毒在我们体内复制,从而有可能缓解人们的COVID症状,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如此重视我们给谁用药呢?最近在加拿大的一个药剂师拒绝按Paxlovid的处方配药患有唐氏综合症和呼吸道感染史的20岁患者。这是明智的公共卫生政策吗?
我问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传染病专家莫妮卡·甘地(Monica Gandhi),为什么那些不想连续几周感觉像垃圾一样的人,那些需要工作或探望脆弱的家人的人,不能轻易获得这种药物?我们广泛使用抗病毒药物来缓解流感症状,为什么不能使用COVID?
她回答说Paxlovid目前已经习惯了预防死亡和住院对我这个年龄段的人的研究表明没有明显的好处在这方面服用药物。
然而,“Paxlovid还有其他好处,”她说。“如果你的病毒载量下降得更快,你可能会更快感觉好起来。但目前还没有任何关于接种疫苗者的研究。”
我对此的理解是,尽管公共卫生指南正在演变,告诉我们COVID现在是地方病,我们可以开始恢复正常,但在许多无益的方面,它仍然将病毒视为致命疾病。
我们不能两全其美。
甘地说,许多医生都认识到,让人们有机会更快地康复的明显效用。鉴于Paxlovid已知的副作用很少,而且很轻微,一些医生很乐意改变规则,给那些在技术上可能不符合公共卫生指南的人开这种药。这在美国是可行的,因为目前由联邦政府买单——他们没有严格检查谁有或没有可怕的合并症。但是Paxlovid很贵。随着联邦政府削减资金,保险公司开始承担药物成本,你可以预期这些资格要求会比现在更严格。
如果欧米克隆疫苗在阻止像我这样的重大感染上被证明无效,会发生什么?我们愿意让永久的疾病成为正常生活的代价吗?
根据迄今为止美国对COVID的反应,我相当确定答案是肯定的——除非人们开始煽动。我们要依靠保险公司的精算师和积极思考的力量来引导我们回归正常,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后果吗?还是我们要坚持让公共卫生官员研究所有可以让我们尽可能少痛苦的工具?
马修·弗莱舍是《旧金山纪事报》的社论版编辑。电子邮件:matt.fleischer@sfchronicl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