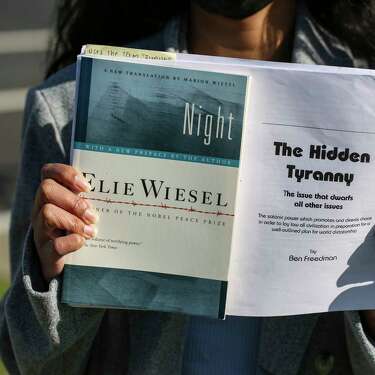我十岁那年的一天早上,我醒来发现一串纳粹标志在我的郊区社区里穿行。它们出现在邮箱上,企业上,我们当地拉比家门前。肇事者在他们的作品旁边潦草地写着“最终解决”和“希特勒的孩子”等口号。那天是赎罪日的前一天,对像我这样的犹太人来说,赎罪日是一年中最神圣的日子。这个时间点不像是巧合。
当时,美国的偏见和反犹太主义对我来说是抽象的概念。我对这个话题的介绍来自于我父亲上大学第一天的故事——他的室友要求看我父亲的犹太角。
他不是在开玩笑。
我爸爸总是把那个故事放出来逗乐。他说,他的室友没有恶意。他们最终成为了朋友。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对美国偏见的理解——是那些受庇护和无知的人的卡通领域,而不是那些精于算计和心怀恶意的人。
暴力是纳粹的专利。他们都是过去的事了,这是我祖父母讲的一个故事。
然而,门口的一束纳粹标志却突然让我开始质疑一切。纳粹也在这里吗?和我一起住?等待时机?
在我那个以白人和黄蜂为主的小镇里,我不是一个很酷的孩子——很少被欺负,但更很少被注意到。我从来没想过我是犹太人能影响我在这个社会等级中的地位吗。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普通的极客:不起眼的隐形人。
如果我一直被人看见呢?
这是一个可怕的想法。偏执是心理上的雷区。我在没有地图的情况下四处游荡。
纳粹十字记号到达后,几天过去了,没有关于它们的创造者的消息。我的恐惧与日俱增。有多少纳粹潜伏在那里?我的家人有危险吗?
每天早上,我把自己锁在浴室里,拿着报纸,急切地想知道最新的消息。没有人回答。
然而,在这一事件脆弱的后果中,有一篇关于纳粹标志的文章。它改变了我的生活。
这是一位专栏作家写的,他是该报的新手。他的名字叫德里克·z·杰克逊(Derrick Z. Jackson),是该报历史上为数不多的黑人专栏作家之一。
我承认,当我看到他的署名时,我10岁的头脑很难理解发生了什么。我是一个相对受庇护的孩子,但我知道,在美国做一个黑人比做一个犹太人要困难得多。为什么一个有着难以解决的种族问题的人会把自己的目标放在背后,去支持一个由相对特权的郊区犹太人组成的小社区?
但他确实做到了。他做得既有力又漂亮——在我看来,他冒着纳粹的愤怒来表达他的愤怒和关切。
读完这篇专栏后,我立刻在浴室的地板上失声痛哭。我仍然无法找到语言来表达我那天的感激之情。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安全。但我知道,在危险地带,有人不需要关心我,也会站在我身边。
我又花了十年时间才弄清楚我想成为一名作家。但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清楚地知道我需要成为什么样的作家——一个有使命感的人,就像我10岁时从一个观点专栏作家那里学到的那样。
我以介绍的方式分享这个故事。我叫马修·弗莱舍,是《纪事报》社论版的新任编辑。
记者不应该有偏见,更不用说公开披露了。好吧,我要分享这个。新闻业对我很重要。这不是智力训练。这不是薪水。这是在告诉一个10岁的孩子有人关心他们的生活和他们存在的尊严。任何误导他们不相信的人都会受到惩罚。
然而,它也必须不止于此。一个公正的社会需要得到政策和行动的支持。当然,这就是事情变得棘手的地方。
在美国历史上最具挑战性的时期之一,我接手了《纪事报》的观点栏目。距离一场试图推翻美国选举结果的暴力政变只有四个月了。警察杀害黑人和棕色人种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暴力的反亚裔偏见正在蔓延,加剧了之前的反拉丁裔、反穆斯林和反lgbtq仇恨浪潮。当然,近60万美国人因COVID大流行而死亡,数百万人变得虚弱,这是政府失败的灾难性影响我们生来就不平等。种族隔离的遗产在美国依然存在,在自由的旧金山和密西西比一样多
在这种社会冲突之上悬着气候变化的镰刀,如果我们不立即果断地采取行动,它就会被砍掉。
这些困境没有简单的答案。答案可能根本不存在。但我们必须设法找到解决办法。
《纪事报》编辑部的最佳尝试将植根于反种族主义,以科学为指导,始终着眼于防止灾难性的气候变化。
我们不可能总是做对。有时你可能不同意董事会规定的政策。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期待收到你的来信。
马特·弗莱舍是《旧金山纪事报》社论版编辑。电子邮件:matt.fleischer@sfchronicle.comTwitter:@MatteFleisc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