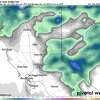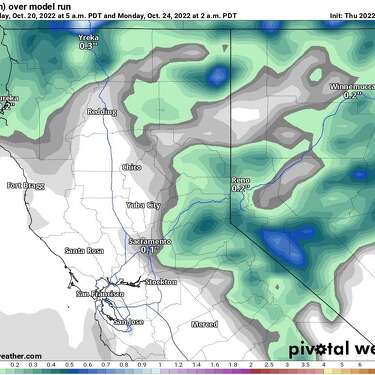W莱利从未梦想过成为一名激进分子。他最初的目标并不是反对南方种族隔离。然而,作为一名20世纪50年代在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县长大的黑人,他发现要拥有自尊和尊严,他别无选择,只能战斗。
十几岁时,莱利加入了这一运动。他组织了抗议和纠察线,在午餐柜台静坐,并与马尔科姆·艾克斯和弗洛伊德·麦基西克等民权领袖交谈。1965年搬到湾区后,莱利参加了1968登录必赢亚洲年旧金山州立大学种族研究学生罢课运动,最终定居在奥克兰。在那里,他曾担任民权律师和活动家,将斗争文化传递给自己的家人,包括他的儿子、电影制作人、说唱歌手和组织者博茨·莱利(Boots Riley),以及他的孙子阿基尔·莱利(Akil Riley),后者去年在奥克兰技术高中参与领导了“黑人的命也是命”游行。
在开始为变革而努力60多年后,77岁的莱利仍在战斗,谈到年轻人寻找集体力量的重要性,并确保一个没有警察暴力、没有种族歧视、人类生命更有价值的未来。
这次采访是“提升每一个声音”的一部分,该系列将年轻的黑人记者与我们社区的黑人长者联系起来,以庆祝并学习他们的生活经历。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旧金山纪事报》(Th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已与赫斯特的报纸、杂志和电视台一起出版了数十篇人物简介。
问:你在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长大,十几岁时成为民权抗议者和组织者。作为运动的一员,在这么年轻的时候站在工作的前沿是什么感觉?
答:我很年轻就开始了。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感觉,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因为我希望我的前几代人做得更多,这样我就不觉得有必要这么做了。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我渴望成为一个孩子,但我不觉得自己能成为一个孩子,因为我对周围发生的事情太敏感了。
参加民权运动的压力很大。但这一直是生活在南方的黑人的困境。这是我在50年代开始意识到我周围世界的困境。我也很喜欢。我很高兴能够坚持自己的个性,我渴望成为集体方法的一部分,一个共同的方法来处理社会中的种族主义,改变的需要,并努力实现我认为成长的一个重要方面,变得足够成熟来处理我周围的问题。
问:你是种族平等大会(Congress of Racial Equality)的领导人,该组织开创了非暴力行动,组织了自由乘车运动(Freedom Rides),最终发展为支持黑人民族主义。你在CORE的工作对你的律师职业道路有何影响?
答:CORE是我在60年代早期加入的一群人,他们把边缘推得更远。也许CORE在某种程度上——对我和与我一起工作的达勒姆周围的人来说——更倾向于以更直接的方式挑战法律、挑战种族隔离和挑战习俗。这些挑战我周围习俗的价值观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并向我灌输了这样的概念:在这个社会中,一个人必须做什么,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公民,才能有尊严,才能尊重你的社区和你的家庭。
问:在你18岁的时候,你主持了马尔科姆·艾克斯和弗洛伊德·麦基西克之间的对话,对吗?
答:我做到了。我和马尔科姆待过一段时间。弗洛伊德·麦基西克是NAACP的律师。他是我的导师。我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一张桌子,他是我想成为一名律师的原因之一,因为我认为他是一个独立的人。他的生计是由他和他的客户关系决定的,而他的客户来自他的社区。这很重要。
在这场运动中,我认识了马尔科姆·艾克斯和其他很多人,但实际上,马尔科姆·艾克斯给我留下的印象成为了我每天生活的一部分。他的哲学中有许多公理被人们使用,但我们都从中得到的是:我们有存在的权利。我们有权利为自己而战。我们有权利挑战压迫我们的制度。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一直带在身边。
问:考虑到你对自由乘车者和午餐柜台静坐所做的工作,让我们有了今天的成就,你是否更倾向于非暴力行动或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进行变革?
答:我不是哲学家,不是甘地方法的追随者。我不是那种说你必须容忍自己被打,然后对别人宽以待人的人。马尔科姆·艾克斯的立场引起了我的共鸣。但是弗洛伊德·麦基西克是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以及后来作为核心组织的领导人和激进律师中明确表示立场的人之一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使用非暴力的策略因为我们不能靠枪支获胜。
在达勒姆的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想办法保护自己。但我们并不是在组织一场与国家、与体制的暴力对抗。非暴力是一种策略。我当时和现在的经验是,在世界历史上,被压迫者能够以非暴力的方式消灭压迫者的情况从未发生过变化。在美国历史上,有很多针对黑人和其他很多人的暴力事件。正是通过对暴力的抵抗,我们所经历的任何变化才得以实现。
问:我们仍在遭受攻击。你认为哪种策略会支持我们今天的解放?鉴于无端的袭击和许多黑人死于警察之手,你认为需要做什么或可以做什么来保护黑人社区?
答:我认为我们在一些地方已经有能力参与政策制定来改变这种情况。但对这个国家的很多人来说,情况并非如此。有很多地方,很多县,很多小镇和村庄,执法不会受到黑人、印第安人或拉丁美洲人政策投入的影响。
但在那些我们有能力通过改革运动参与到市议会、学校董事会的治理过程中的地方,我们必须参与到这些事情中来。我们还必须围绕这些问题进行公开对抗。我们必须静坐和市议会会议,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这些,我们的声音就不会被听到。我们必须举行大型示威活动,动员民众,因为这是提高人们对这些问题认识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我们应该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来做到这一点。
问:作为一名律师、活动人士和我们社区的长者,你如何看待乔治·弗洛伊德案的有罪判决?你认为正义是什么?
答:这一裁决受到欢迎。我认为这是向前迈出的一步,但这并不公平。这并不能让乔治·弗洛伊德复活,也不能减轻我们在全世界看到这段视频时的悲痛。这并不能解决我们与这个国家的种族主义制度和警察文化之间的冲突,警察文化继续参与谋杀黑人。
正义应该是全国范围内平等公平的就业实践。正义看起来就像是我们社区里更多的就业机会。正义看起来像是对多年来存在的虐待的补偿。正义看起来就像我们社区的住房。正义应该是体面的医疗保健,正义应该是更好的教育和受教育的机会。结构性改革需要一种不同的哲学视野和对世界的认识。因此,司法将会是一个非常不同的社会,一个非常不同的警察力量。
问:你是一位父亲和祖父。你害怕生孩子吗?你是如何让他们为世界对他们的反应做好准备的?
答:我一直意识到,在这个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他们的生活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我的孩子们不得不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他们的父亲从事政治活动,挑战制度的本质,他们开始理解这一点,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主要在奥克兰,作为一个单身母亲抚养两个黑人男孩是一个挑战,因为只要你走到街上,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我想让我的孩子们意识到,因为他们是黑人男孩,他们必须考虑自己的安全,但不能逃避斗争,不能逃避与朋友和社区的交往。我认为他们学到了这一点。他们学会了如何应对和处理这个系统,这个系统让他们和朋友一起寻找快乐,和家人一起寻找快乐,找到和其他人一起行动,做出改变的能力。
问:对于那些还没有完全投入工作的年轻人,你有什么建议?
答:我想在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中提出这一点,当我们开放地看待一个新世界时。至少从青春期到成年早期,也就是20多岁,我们有机会挑战这个体系,不接受周围的事物,寻求改变。我想真正的建议是,要以开放的心态去寻找一个你能融入的世界,并让这个世界对你做出回应,这样你就不必只想着如何改变自己。世上没有钻不破的石头,没有穿不透的墙。不要接受限制。
“提升每一个声音”将年轻的黑人记者与我们社区的黑人长者联系起来,庆祝并学习他们的生活经历——加深与过去的联系,让我们所有人都为更美好的未来做好准备。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旧金山纪事报》已经加入了赫斯特在全国各地的报纸、杂志和电视台,发表了数十篇个人简介。
《提高每一个声音,歌唱》由詹姆斯·威尔登·约翰逊兄弟和约翰·罗莎蒙德·约翰逊兄弟于1900年创作,最初是一首写给小学生的诗。不久,这首歌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的活动、黑人教堂和社区会议上传播开来,每次被演唱时都获得了突出的地位。被称为“黑人国歌”的《提高每一个声音和歌唱》是一个胜利的故事,记录和承认过去,同时向自由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