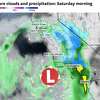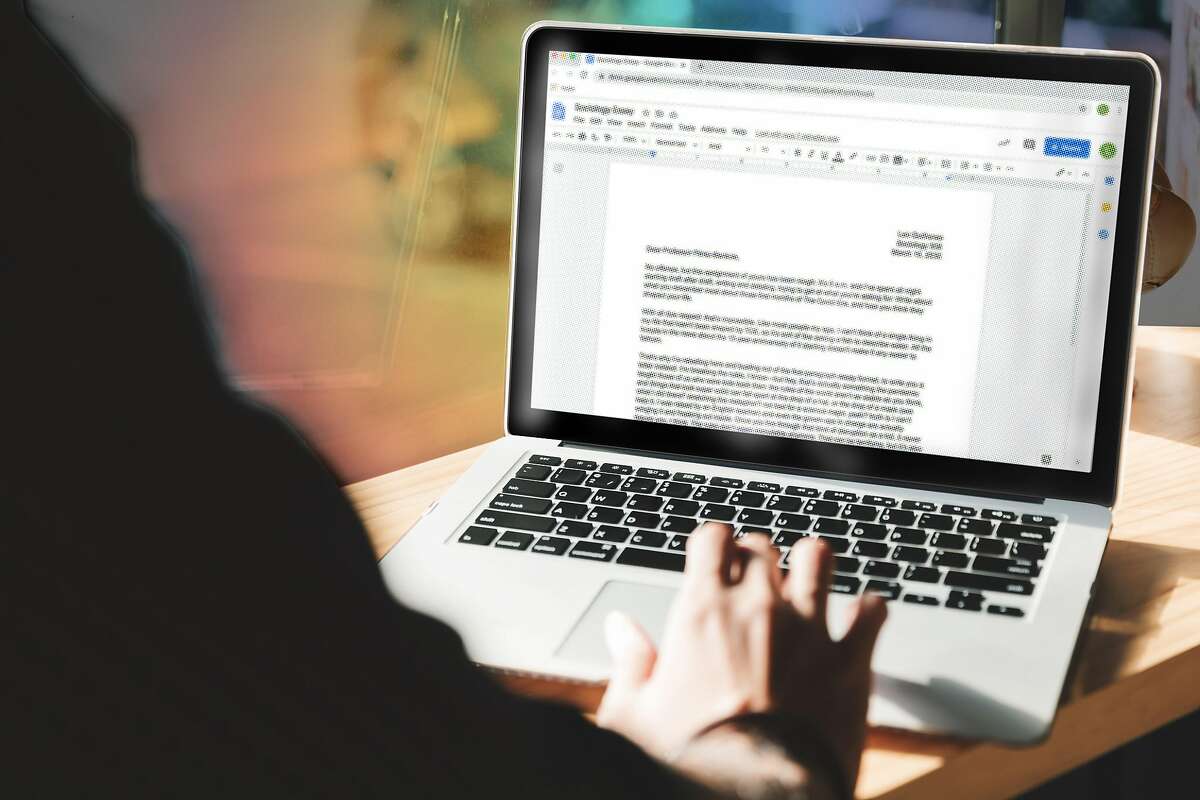
卡罗莱纳·德·罗伯蒂斯为《频谱一代》绘制的插图。Leo Quiñones在2030年为社会学308写了一篇文章。
来自Getty Images元素的编年史照片插图狮子座醌类
社会学308
2030年3月15日
尊敬的pembrorez - bankole教授:
无意冒犯,但你的任务太难了。现在是凌晨5点,我花了一整夜的时间一稿一稿地写,写,删,试图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写下你对新冠时代头几个月印象最深的事情,以及你认为它们如何影响了你的生活。
恕我直言,那是不可能的。像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我想不出我生命中有任何一件事不是由TCE塑造的,所以这有点像让鱼描述水。新闻中关于它成立10周年的所有喧嚣并没有使它更容易理解。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在这里反叛,打破五段文章的格式,给你写一封信。我知道我打破了规则,但是,嘿,这实际上是大流行教给我们这些当时还是孩子的人的东西:世界的规则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稳定,看起来超级坚固的东西可能会在帽子掉下来或面具掉下来的时候分崩离析(看到我在那里做了什么吗?延伸隐喻?对理科生来说还不错吧?事实上,我也没办法(我是由一位英语老师养大的),甚至那些负责的成年人也在即兴发挥,内心也很害怕。我认为,一旦你在小时候经历过那种混乱,它就永远不会离开你。规则似乎不再是一成不变的了。这可能很可怕,但也很神奇。
我知道我是泛化的,当我只能代表我自己说话时,代表我们这一代人说话可能是不好的形式,无论如何,你们仍然可能因为我没有按照指示做而让我的文章不及格。
我请求你不要这么做。
我保证,我会认真对待这个任务的。
只是这是我唯一能找到的解决你这个大问题的途径。
外面的人都知道这个故事。至少对我来说,这是我内心的感受:好像整个世界已经决定分崩离析,但又拿不定主意是要像鸡蛋一样融化、破碎还是破裂,好像它不太了解自己的本质,所以它只是在这种和那种溶解之间摇摆不定。但奇怪的是,我不记得当时有多害怕。生气,当然,我经常看不到我最好的朋友,即使是这样,我们必须讨论面具,要站在外面,要短,我不能在当地公园,爬单杠上,远程学习是如此愚蠢和无聊和混乱,我仍有出现,我五年级毕业是一堆小盒与我所有的同学在屏幕上看起来过分打扮的和充满希望的。直到后来我才明白他们中的一些人经历了多少。他们没有食物,失去了父母,或者被赶出了家园。在那些小小的网络盒子里,我还没有看到所有的悲伤。我们花了很多年才理解彼此的故事。事实上,我认为我们还在学习理解。
不管怎样,我绝对是幸运的。我妈妈整整一年都把我们关得严严实实的。家庭旅行被取消。一切都被取消了。我们的房子成了我们的世界。这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有两个父母,我的妹妹和我,还有我的奶奶,她飞到奥克兰,在这一切开始的时候搬来和我们住在一起,因为她一直住的地方不安全。所以我们的房子很拥挤,感觉就像一个不停的派对。
奶奶逗我们笑,大声给我们读搞笑的故事,我们熬夜看电影,学习如何做菠萝倒立蛋糕,我们比以前有更多的屏幕时间,而妈妈们则忙着远程工作,把一切都放在一起。
六月的一天早晨,我们都坐在餐厅里,报纸摊开,吃着炒蛋和熏肉。大人们谈论着抗议活动,谈论着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的大照片,她高举着拳头,带领一大群人从奥克兰港前往奥斯卡·格兰特广场(Oscar Grant Plaza)。
在那一刻,我试着不去理会,就像我通常一提到奥斯卡·格兰特的名字就会做的那样。
有一次,妈妈告诉我,奥斯卡·格兰特在她怀我的时候被人谋杀了,事发地点离我们家不远,虽然她没有补充任何类似的话,我在想,有一天你也会是这样,但关于他的死,他的名字,仍然有一些凄凉而私密的东西,在我11岁的时候,把我掏空了。所以我一吞下早餐,就伸手去拿电子游戏。但是大人们继续说话。
“这让我想起了60年代,”奶奶说,“但也一点都不像。”
“你是什么意思?”妈妈说,她也吃完了饭,坐在桌子一角的机器前缝口罩。
现在我在听,假装没听见。奶奶当年有一些非常不可思议的故事,比如冒着生命危险在密西西比州登记选民,游行,被捕,从扔进她睡觉的房子的玻璃窗的燃烧弹中幸存下来。她知道一些事情。
“参与的程度,”她啜着咖啡说。“街上有那么多白人,看起来真的很投入。也许这可能是一个转折点——尽管我们不应该经历这么多恐怖才走到这一步。”
我记得阳光洒进房间,照亮了她的手,她的手围着咖啡杯。也许我会选择这段记忆来代表我早期的COVID。
两只阳光明媚的手,皱巴巴的,美丽的,捧着温暖。
我希望我的奶奶能在这里看到过去一年的胜利。并不是说任何事情都能证明恐怖是正当的。我的意思是,仅就COVID而言,无法用言语形容。50万人。我无法理解这些,我是个数学专家。我很高兴会有一个追悼会。我知道全国都在争论把它变成虚拟的而不是实体的,但我认为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总统的想法是对的。这段历史只是不属于一个城市或一个地理位置。它的记忆应该无处不在,又无处不在,真实而缥缈,锚定而又超越。虚拟的。 Like so much of our lives now.
我查了“虚拟”这个词的词根。原来它来自拉丁语博洛尼亚卓越,潜能。因此,虚拟体验保留了事物的本质,它的卓越,而不保持相同的物理形式。虚拟与IRL是一个过时的框架,真的。
这是一个错误的二元,就像我们对性别的看法一样,而且,你知道吗,我们这一代人看透了这两者。也许我们应该被称为没有双星的一代,或者频谱的一代,或者别的什么。哈!问题是年轻一代从来没有给自己起过名字。除非这是另一条旧规则我们可以爆炸。
也许这就是我从TCE中学到的:我们不必害怕改变。这并不是什么一无所有的反乌托邦未来。那些老故事太懒了。如果失去了一切,你可以绝望地举手投降,然后呢?看看气候危机。我们再也承受不起那些绝望的故事了。
更复杂的真相带着我们所有人,并试图看清它。更复杂的事实是,我可能属于不同的一代人,但我也是我祖母的孙子,我们都必须继承前人的遗业,把工作继续下去。
对我来说,虽然我一直在与种族主义作斗争,但我的主要工作是在一个不同但相关的战线上。在这个生态崩溃的时代,我是一位有抱负的有色人种生物学家。我做过关于崩塌的梦,那是可怕的真实,我听到树木在燃烧时尖叫,海洋在哀号,唱着毒歌。它让我早上起床,整夜不睡,钻研分子构型和微积分函数。也许是害怕,但也有决心,因为还有工作要做,我打算在有生之年参与其中。作为一名科学家,我会成功吗?
它会产生影响吗?我不知道。但尽管我很害怕,我还是得试试。
我的妈妈有一句谚语,用西班牙语挂在墙上:El que no sabe de dónde viene no sabe dónde va。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人,也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
好吧,除了性别化的措辞,它很深奥,对吧?我们回顾过去是为了了解我们要去哪里,确保我们有一个地方可去。
现在我觉得闸门打开了——记忆、思想、想法、火花。但是我快没地方了!搞什么鬼?你曾经在虚拟课堂上说过,最好的思考实际上并没有给我们带来答案,而是给我们带来更深层次的问题。我感觉到了。它会永远持续下去吗?这是一件好事吗?
还有一个词源:“短文”这个词来自古法语,意思是“努力,尝试”。
如果我写不完这篇文章怎么办?
如果我才刚刚开始呢?
你的,
利奥

卡罗莱纳·德·罗伯蒂斯是湾区作家,她的小说《坎特拉斯登录必赢亚洲》于2019年出版。找到她的写作www.carolinaderoberti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