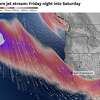这是一个旋转木马。使用“下一步”和“上一步”按钮进行导航
那是1982年,“无家可归”这个词刚刚慢慢进入公众意识。乔·威尔逊(Joe Wilson)是那些在经济衰退和社会服务支出大幅削减的情况下无家可归的人之一,他在旧金山的人行道上下了几周的大雨,最后来到了好客之家(Hospitality House)的避难所。
这标志着他在街头生活的结束——最终,这为旧金山最早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咨询和临时床位的地方之一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酒店成立在爱的夏天为那些涌向旧金山寻求和平与爱却遭遇艰难时光的年轻人提供庇护。从那以后的50年里,它已经成为该市无家可归者服务网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现在每年为大约2万人提供服务。
2017年,62岁的威尔逊成为了酒店的执行董事,他已经是酒店最成功的人物之一。这个曾经在这家非营利组织的屋檐下避难的人,现在不仅管理着30个床位的庇护所,还管理着艺术、就业和咨询项目。他总共管理着55名员工,年度预算为450万美元。
“乔很聪明,他有真实的生活经验,他激励着每一个为他工作的人,”他说Sam Dodge是公共工程部无家可归者政策的负责人并帮助建立了该市的无家可归者和支持性住房部门。“当我们都知道他将负责招待所时,我们想,‘好吧,现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你必须对他早年所做的事情有一个深刻的理解,他后来没事了。他有这种品质,可以胜任他现在的工作。”

自2012年以来,威尔逊一直是好客之家的社区组织者,在他的项目中,他散发出几种品质:他朴实无为,街头强硬但有礼貌,从不忘记自己的贫困出身。
“他是这里建筑的一部分,是一个传奇,”在好客之家帮助监督志愿者队伍的菲吉斯·卡特(Fagis Carter)说。而且“他当然不接受任何胡扯。”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很有帮助。喜欢,永远。”
威尔逊对这样的声明只是耸耸肩。
“这里的街道上每天都有奇迹发生,有人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有人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说。“我就是一个例子。我以前只是睡在地板上的垫子上,现在是我在管理这个组织。
“这种可能性有多大?”我不认为任何一天都是理所当然的。”
威尔逊走到今天这一步,经历了贫穷、绝望和在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的几段时间,经历了曲折。
他在密西西比州和芝加哥长大,母亲是单身,靠做护理助理勉强维持生活。他在学校成绩优异,后来来到加州斯坦福大学(Stanford)学习历史和经济学。他从学校休学很长时间,回到芝加哥照顾生病的母亲。1979年,当他被告知母亲去世时,他辍学了。
他说,这是一个关于家庭内讧的复杂故事,他在2008年与母亲重新取得了联系,但相信母亲已经离开的打击使他偏离了轨道。
在帕洛阿尔托开过出租车,在旧金山的一家自助餐厅工作过一段时间后,威尔逊最终失业,身无分文。1982年,他流落街头。为了避寒,他每晚都在市场街的Jack in the Box里喝着廉价咖啡,然后在好客之家(Hospitality House)找了个床位。
“招待所可能是我第一次听到‘无家可归’这个词的地方,因为那时候它刚刚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东西,”他说。“这个地方比我去过的教堂更受欢迎。我觉得自己被接受了。”
在好客之家的避难所睡了一段时间后,威尔逊成为了一名志愿者,然后是同伴咨询师,然后是一名员工,最后是避难所的主管。几年后,他离开了,成为了一名青年倡导者和工会组织者,五年前,他又回到了好客之家,从事社区组织工作。
保罗·博登,几十年来旧金山最重要的无家可归者活动家之一我在招待所遇见了威尔逊。博登当时在收容所工作,给威尔逊找了一份清洁城市公交车的工作,并建议他重新站稳脚跟。他说威尔逊是他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之一。
博登说:“在那个避难所工作,你必须能够在一个非常混乱的环境中工作,人们的状况非常糟糕。”乔只要一出现,就能使房间里的人平静下来。
“如果你带着尊重和人们交谈,而不是像纳粹指挥官那样对他们吼叫,他们就会冷静下来,”他说。“这就是乔擅长的。他很有同情心,但又不是个懦夫。”
作为执行董事,意味着威尔逊必须调整他的人际交往能力,以适应管理一家大型非营利组织的行政工作。他主持了一个紧张的会议,但真正的接触仍然是面对面的。
“好吧,现在怎么办?”前几天,威尔逊问一位浑身湿透的中年男子,他坐在土耳其街招待所的行政办公室旁边,神情茫然。这个人,肯尼斯·“柯比”·麦科尔,伸出一只手说话了。
“汤和苏打水,”麦科尔嘟囔着,用朦胧的、不确定的眼睛向上凝视着。
威尔逊跪下来,紧盯着麦科尔的脸,强迫他集中注意力。“不喝苏打水,”他说。“它们对你不好。跟我来。”
他开始把麦克科尔带到离莱文沃斯街一个街区远的招待所接待中心。麦科尔摇了摇头。“只是汤,”他说。“没办法去旁听席。只是汤。”
其他人可能已经放弃或变得说教。威尔逊躲进办公室,拿了一包饼干和两条蛋白质棒出来。他轻轻地拿过麦科尔手里攥着的空薯片袋,把食物放了进去。
威尔逊说:“当你准备好了,你就来培训中心。”McCole点点头。他摇摇晃晃地走上特克街,威尔逊叹了口气。
威尔逊说:“我们必须把他和城市无家可归者服务小组(HOT)放在一起。”“也许我们可以再来一次。你不能就这么放弃。你必须记住,事情是可以改善的。”
走了半个街区,麦科尔手里的食物掉在地上。威尔逊走过去,拿起包裹,把它们放进麦科尔的口袋里,然后拍拍他的背,麦科尔又摇摇晃晃地走开了。
“这并不容易,”威尔逊说。“但你必须永远记住,永远没有希望。”
凯文·费根是《旧金山纪事报》的特约撰稿人。电子邮件:kfagan@sfchronicle.comTwitter:@KevinChron